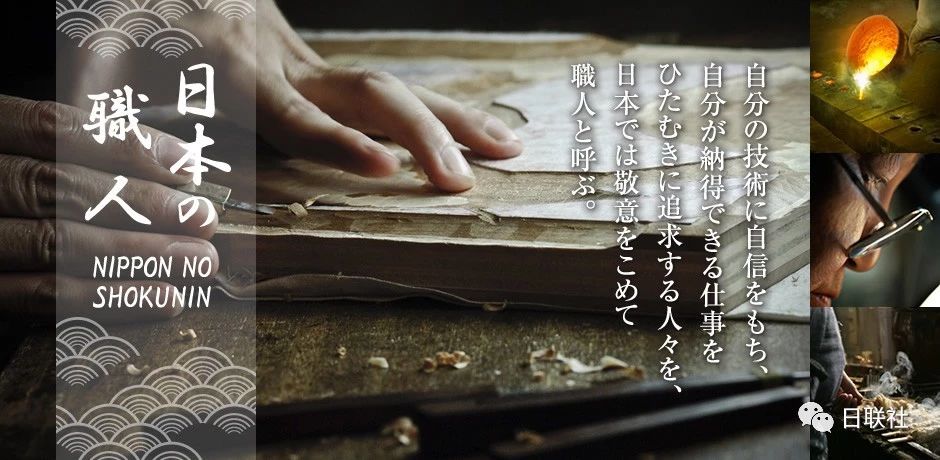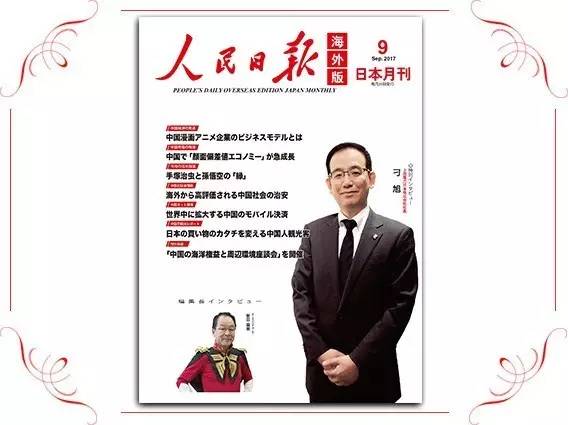日本的匠人(日語叫 “職人”)精神,無論是到任何時代都閃耀著獨特的光彩,令人動容。
盡管匠人精神是最近幾年備受關注的詞語。但其實它早就存在于中國。《莊子》的 “庖丁解牛”,就說的是一位匠人。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這位廚師不僅分解牛的技術高超,動作還合乎音律。他是這樣解釋的。“我是精神和牛的接觸,而不用眼睛去看,依照牛體本來的構建。用很薄的刀刃插入有空隙的骨節。十九年了,我的刀刃還像剛從磨刀石上磨出來的一樣鋒利。”心到、神到、就能達到登峰造極、出神入化的境界。
日本之所以如此尊重匠人精神,是有時代淵源的。早在飛鳥時代,圣德太子就曾將修筑宮殿的土木工匠冊封為“左官”和“右官”。
到了奈良時代,日本佛教興起,不管還是官府還是民間都設立了很多寫經所,天平年間還有專門的寫經司。寫經所里的校正師、裝卷師、等都是匠人,統一由“大經師”管理。
到了平安時代,日本鍛冶業興盛,刀劍師、甲冑工匠都是令人尊敬的職業。由于貴族對衣著的顏色和質地的要求越來越高,所以紡織染布業的杰出人才也是人人稱贊的匠人。
在鐮倉時代,日本還有一種叫做 “職人歌合” 的藝術形式,專門以職人的生活為題材制作和歌。現存于世最早的 “職人歌合” 是1214年的《東北院職人歌合》,有五番本和12番本,前者描寫了10種職人,后者則是24種。在五番本里提到的職人包括醫師、鍛冶、磨刀、巫女、漁師、陰陽師、木匠、鑄物師、博打、商人。到了室町時代,職人的種類也大幅擴大,于是就有了《三十二番職人歌合》和《七十一番職人歌合》。在《七十一番職人歌合》里登場的職人共有142種。
這種記錄在1690年的《人倫訓蒙圖彙》一書中里達到了頂峰,共收錄了460多種職業。
法國人類學家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曾于1977年到1988年間先后五次造訪日本,他說,自己寧可犧牲了造訪神社和博物館的機會,也要盡量擠出時間和日本各行各業的工匠們交談。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認為,日本的匠人的工作,被視為是一種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的具體展現。就好像某些能劇推崇日常家務,并賦予它們詩意的價值一樣。
藍染匠人林滿治在《東京下町職人生活》里口述,“說到底,我們還是做工匠的性格,不會跟人算得那么清楚。成功染出作品時的喜悅,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的。如果藍的心情不好,那么染出來就不漂亮。” 豆腐匠人熊井守在《東京下町職人生活》里口述,“動作太粗魯的話,豆腐的臉色就會很難看。細心做出來的木棉豆腐,肌理就會細致有光澤。”
這兩個人的口述其實都證實了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認的分析,匠人與自己所維持的工藝非常親密,不僅賦予了它們以詩意,還賦予了它們以人格。這就是匠人精神的表現。
匠人精神的另一個表現是固執,或者說是頑固。他必須堅持自己的追求,必須恪守祖傳的工藝,而不能像銀行等機構那樣顧客第一主義。匠人如果想取悅顧客,就會有所妥協,改變自己的工藝。然而不管是在材料的選用上,還是工藝所需的時間上,都不能差不多就行。
匠人精神的第三個表現就是對 “品” 的追求。這種 “品”,包含著品位、品格、品性。
在工業化時代求快、浮躁的整體節奏下,批量生產的流水線制作的確對傳統手工藝者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如今日本的很多傳統工業也面臨后繼傳人青黃不接的境地。為此,很多有歷史的傳統工業都開設了藝術研究所,接受年輕人短期見習。畢竟在日本社會,匠人的地位還是很高的,雖然有超市、百元店存在,但限量的手工制品依舊倍受推崇,所以向往做個匠人的日本年輕人也不在少數。
推崇陰翳之美的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還說過這樣一句話,“藝術家無論怎樣怯懦,也要安于自己的天分,精益求精地研習藝術。這時候,就會產生為藝術而不惜舍生的勇氣,不覺間對死就有了切實的覺悟。這才是藝術家的勇氣!”
只要匠人魂常見,日本的傳統工藝就會不朽,只要有“藝術家的勇氣”,日本的傳統工藝也能發展成時代需要的尖端產品。想至此,筆者也感覺實在是不需要為日本傳統工藝的傳承而擔心。但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工藝呢?
文/ 蔣豐(《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