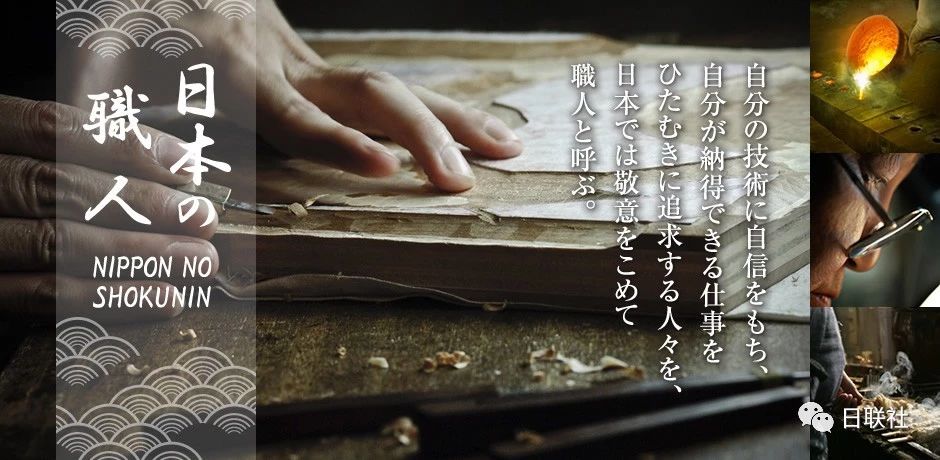在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掀起單邊主義浪潮的背景下,全球秩序將會發生深刻的變化,我們必須要清楚地認識到,這場“游戲”的參與者遠不止中美。橫沖直撞,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就像是闖進瓷器店的大象,沒有哪一個板塊、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區域、哪一個聯盟能自外于特朗普帶來的沖擊。
所有的國家都要思考,昨天習以為常的玩法,還能否繼續走下去。就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歐洲各國,都開始另懷心機,前段時間法國總統馬克龍和特朗普的爭論就是這種微妙局勢的體現。
隨著美國的自愿“退群”,世界將從“天下共主”演變為“春秋戰國”,合縱連橫成為大勢所趨,區域性的政治經濟聯盟也變成下一步的發展趨勢。從經濟總量而言,除歐美外,第三極將是東亞經濟圈,而東亞經濟圈能否形成的關鍵,取決于中日韓三國,其中又以中日關系尤為重要。
對于日本而言,在美國退出由其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并以對日本汽車加稅作為威脅的背景下,穩住與另一個重要貿易伙伴中國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避免與中國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等地發生消耗性的競爭,甚至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合作,變成了日本的當務之急。
戰略最講究天時、地利、人和,如今天時地利齊備,戰略中心就聚焦于“人和”之上,所謂的“人和”就是中日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互補性有多強?究竟能否走向深度的經濟合作?
談及中日關系,無論是一衣帶水也好,一衣帶血也罷,中日的文化糾葛與淵源,已有一千余年。在全球經濟的舞臺上,中日同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本次安倍訪華,其實并非毫無預兆。從去年年底開始,中日就開始緩和對抗的氛圍,友好之聲從各個渠道傳出,今年年初,中日雙方就開始進行各個等級的互訪,做好了鋪墊,就等安倍從“羽田的青空”踏空而來。
論及原因,此次安倍訪華,既有外部的壓力,也是雙方合作的必要。美國帶來的世界格局變化無需贅言,朝核危機的持續升級及其最終富于戲劇性的解決,使得東北亞地區安全緊張的紓解以及區域一體化再度成為可能。在此過程中,作為利益相關方的中日兩國皆不可能選擇缺席,相互協調、坦率交流的迫切性被大大提前。
1、中日關系考:看60年也要看2000年
回首19世紀以來跌宕起伏的中日關系史,兩國自2012年以來的外交困局,雖然被稱為“戰后最緊張的狀態”,和曾經的兵戎相見比,只算得上是茶杯中的風暴。這場風暴迎來轉機,除了外部的壓力,其真正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轉折,是兩國在經濟體量、軍事實力乃至全球影響力方面出現的不可逆的結構性翻轉。
原被任命為亞洲司司長,后改任為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在1989年一篇紀念周總理的文章中有過這樣的記述:“周總理曾教導我們,對日本既要正視60年,但也要考慮兩千年。從甲午戰爭算起,日本侵略我們長達60年,中國受到了無可估計的損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從漢唐以來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人從人生哲學、經濟文化、到生活習慣,和中國都有切割不斷的聯系。”
談到中國的近代史和改革開放,離不開日本。日本跟中國一衣帶水,隔海相望,不能說同種,但絕對同文。直到現在日本一直承認中國是它的文化母親,這不得不說是日本文明的過人之處。
觀察中國周邊的國家,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凡是自信欠缺的國家,不管昨天跟中國如何友好,比如說南北韓、越南等,它們是最典型的漢文化覆蓋的國家,當初基本上都是中國的文化飛地,在千邦進貢、萬國來朝的時代,甚至可以說就是中國的屬國。除了把漢字作為官方語言之外,孔廟、科舉、禮制、官制等,幾乎使全盤中化。但只要條件合適,它們的第一個舉措就是跟中國切割,廢除漢字。
我們曾經幫助越南建立政權,最后胡志明坐穩以后,他是最積極的去漢化推動者。朝鮮、韓國不外如是。這些國家我都經常去,我在漢城就看到,電視上講儒學的老先生是非常受歡迎的,而且每逢盛大節日,大家身著的服裝都帶有明清兩朝的影子,行走坐臥,謹遵法度。但就是這樣一個深受中國文化浸染的國家,不僅把文字改了,甚至是把首都的名字也從“漢城”改成了“首爾”,仿佛“漢”成了他們的心頭病。更有意思的在于,韓國不僅不承認文化上的源流,甚至還想成為中華民族的爹。孔子是它的,孟子是它的,端午是它的,中醫是它的,甚至24節氣也是它的。這個成了網上大家爭論和調侃的笑柄,這也算是另一種的“文化自信”罷。
越南同樣如此,我到越南去的時候,感覺這里簡直比中國還中國。所有的建筑全是中國明朝時候的建筑,文廟、武廟、國子監,還有宗祠,全都是中國式的建筑。后來我專門考據過。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他的船是從長三角起航,沿著海岸線走,到了北部灣,再沿著中南半島走,一路都是打尖和停留的地方,最后再跨過中南半島開始駛向印度洋。而且鄭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到過的而且都是第一個到的國家就是越南,中國的文化千百年以后還繼續在當地發揮著巨大的影響。
與這些國家不同,日本始終承認自己的文化源頭,這很有意思。日本人不僅承認中國是它的文化母親,而且幫助中華民族保留了我們最偉大的民族記憶,就是漢唐盛世。現在的中國已經找不到唐朝了,只有文字里保留了唐朝的雍容華貴,大國氣象,千邦進貢、萬國來朝;保留著百萬人口的全球最大都市長安,“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的那種盛景。包括當年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到長安留學,返程途中據說船沉溺死,李白長嘆寫下了《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
李白當然是天才級別的人物,提起筆來一揮而就,留下了當時中日關系最直觀的寫照。我經常去日本,我每次去,特別是到關西,仿佛夢回唐朝,不僅是建筑,像京都,唐昭提寺廟,還有它的起居生活,還有禮儀,穿著,房間里的榻榻米等各種形式,都是學習的古代中國。打坐參禪,包括茶道酒道、吹拉彈唱、詩詞歌賦等,都一直保留了下來。
第二個就是文字。日本脫亞入歐、明治維新以后,向西方看齊,它認為亞洲是落后的代表,要向歐美看齊。伴隨它學習歐美的過程,中國的漢字已經不足以接納、描述和包容更多的歐美詞語。日本沒有像其他的國家全盤西化,把漢字否定掉,重建一個文字就完了,日本人在漢字的基礎上,創造了片假名,用以表述外來詞匯,比如說的士——taxi,直接用譯音;比如說絲綢之路,シルクロード。所以現在日本的文字由三部分構成,一個是日語漢字,一個是拼音文字假名,包括平假名和片假名兩類。
看起來不兼容的東西,在日本文字里面構成了一種非常有趣的文化。比如像我們這代人喜歡唱的《北國之春》,它就是由平假名、片假名、外來語一起構成,但是讀起來照樣是一幅風景畫。
前兩天我又去了一趟日本,正是扶桑秋色,“扶桑正是秋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卻折垂柳送歸客,心隨東棹憶華年。”少時讀魯迅詩,知詩美,但卻不曉詩意,更不用說詩境。因為在那以美為剿殺對象的陰郁歲月,個體的審美意識被大大壓抑,況且眼界不開,怎么也想象不岀日本有什么美法,而且是“秋光”時節。這次專選深秋,直奔扶桑紅葉而來。身臨其境,滿目爛漫,不由人頓起“生如夏花之絢爛,逝如秋葉之靜美”,感造物主之神奇,嘆人生之須臾之嘆矣!這時候才豁然開朗,終于明白“扶桑正是秋光好”,好的至境就是“楓葉如丹照嫩寒”。順帶的收獲是,終于明白,一旦去掉“斗士”的外套,作為人的魯迅的確是一個偉大的詩人。
對比魯迅詩與李白詩,兩位相隔一千二百年的文化偉人,留下來的筆墨里仿佛有著興衰離合的喟嘆。什么叫作一衣帶水?什么叫作水乳交融?盡在這兩首詩中。
曾經日本是中國最虔誠的學生,成百上千的日本遣唐使在長安城中學習交流、吟詩作賦,甚至陪著李太白一起喝花酒,這一批批留學生學成歸國后,把一套完整的盛唐氣象帶回了日本,宗教、文學、藝術、建筑、民俗風情、政治典章無所不學。
而二十世紀初,伴隨著甲午戰爭的潰敗,大夢誰先覺,無數中國的有志青年奔赴日本,以日為師,探索救亡圖存之道。然而,當時的日本,教給中國的除了救亡外,影響更深遠的其實在于啟蒙,如李澤厚先生所言,救亡與啟蒙是中華民族近代的兩條主線,日本比中國早一步開眼向洋看世界,早一步脫亞入歐,徹底變革掉幾千年來這套內循環的、高度穩定的、滯后的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開始接受西方的邏輯與概念。中國作為后來者,在前進的過程中,日本發揮了至關重要的變壓器的作用。
政治、經濟、文化、物理、科學等等,這些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表述,其實都是從日本流向中國的。“干部”,“群眾”,甚至“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這些詞都來源于日本。
日本有一個特點,它崇拜誰就徹底學習,要么全盤中化,要么全盤西化,它照搬,但照搬到最后,卻沒有丟掉自己的東西,這就是“洋風和魂”。
1200年前中華民族給了日本一袋面粉,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人把中國的面粉做成了包子、餃子,包上了西方現代文明的肉餡,中國人從日本那邊照單全收,給養了中華文明的現代化之路,真可謂一飲一啄,自有天意啊。
回首日本跟中國剪不斷理還亂的淵源,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文化有幾個特點:第一、它善于學習,而且要么就不學,要學就徹底地學習,毫不保留;第二、它承認自己的源頭,不像一些國家欲蓋彌彰,羞羞答答,譬如韓國。第三、因為日本資源匱乏,危機意識很強,所以幾千年來一直把精細化、極致化當成一種民族精神,甚至成了民族之魂,這也是它今天能夠致力于世界屹立不倒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這點非常值得中國學習。
2、菊與刀:日本的民族性
回到日本的民族性問題上來,也就是,看起來溫文爾雅、文明昌盛的民族,為什么這么野蠻?在20世紀上半葉成了屠夫,成了魔鬼,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
這個問題一言難以蔽之,我想講兩條原因。
第一條,從18世紀開始到20世紀上半葉,整個從歐洲美國帝國主義國家開啟的邏輯和游戲規則,就是弱肉強食。最早從500年前,整個西方殖民史海上馬車夫,荷蘭、西班牙、葡萄牙開創的就是武力爭奪,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達·迦馬,一直到美西戰爭,西班牙的無敵艦隊,被英國大不列顛給干掉,英國人取代了西班牙,幾乎控制了美洲大陸,最后成了日不落帝國。當時整個人類長達四五百年踐行的就是叢林法則,就是殖民統治、強盜邏輯,誰搶到是誰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整個亞洲有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一個就是俄羅斯,很多人不太了解俄羅斯,我去過俄羅斯很多次,俄羅斯本質上是搭上了帝國主義殖民化末班車的最后一個所謂歐洲國家。
回到日本,日本本來也是被宰割的對象。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人是針對著中國來的。伴隨中國被打敗,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國家,賠款納降,然后門戶開放,整個西方都蜂擁而入。這時候的日本也面臨民族存亡的危機,但英國人已經顧不上日本,中國這個肥羊就夠它吃的了。而且英國一家吃還不夠,全世界的帝國主義都來分食中國。
當時有一幅漫畫畫得非常好,叫作“屠龍圖”。中國是條龍,十幾個帝國主義的列強,一個抓頭,一個抓尾巴,切割中國。這個時候日本讓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看上了。就是日本的歷史上有名的“黑船事件”,一艘美國艦隊悍然闖關,強迫日本門戶開放,日本從此驚醒。
日本人有個特點,善于反思,反思的結果,日本人采用了什么方法呢?要么我被宰割,要么我宰割別人,日本人就堅信這一條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想不被采宰殺,就要成為宰殺者隊伍中的一員。所以這個時候日本就開始全盤西化,明治維新。
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國家的經濟實力十分有限,它要實現原始積累,最好的辦法不是巧取豪奪,而是明火執仗,也就是踐行殖民化政策,而殖民化中它最大的對手就是中國。所以這時候出現一個分界點,就是甲午戰爭。
1860 之后的 30年,大清帝國其實看起來還像個樣子,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經崛起,自 1860 年代開始的,推動了被歷史學家稱之為“同治中興”的改革,官僚體系的重新注入活力,基本現代化部隊的建立,在外交上總理衙門的建立使外交步入了專業化,工業上、教育上、地方治理上一切都看起來在朝好的方向發展。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時開始的明治維新一樣,似乎標志著一個古老文明面對現代挑戰的應變。
中國和日本同為專制政體,改革同樣由精英階層自上而下地推動,而在才智上,李鴻章一代也絕不遜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1894 年中日正式交戰前,這兩個國家誰的成功更顯著,似乎仍未有定論。北洋艦隊的駐地我也幾乎都去過,譬如劉公島等等,而且很多中國這邊的艦長跟日本艦長還是同學,都是從西方留學歸來。但是非常遺憾,清王朝已經腐敗透頂了。日本則是民族存亡關頭,勵精圖治。同樣的武器,不同的人,不同的體制,最后中國戰敗,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甲午海戰、八國聯軍之戰,之后就是漫漫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國一步步地陷入深淵。
我這次到日本專門去了下關,李鴻章跟伊藤博文簽約的地方。當時伊藤博文跟李鴻章私交很好,互相非常欣賞。現在史學界對于李鴻章有一股平反的浪潮,是非功過究竟如何我們還不好說。但當時,李鴻章面對這么一個破爛的攤子,真是沒辦法談判的,我這次去日本也實地調查過,他可以說是盡了自己的力。
當時伊藤博文開口就要四億兩白銀的賠償,就是一個中國人一兩白銀。李鴻章使盡了渾身解數去談,伊藤博文幾乎拎著他脖子要他簽約。這個時候出來一件事情。日本的激進分子還嫌要的不夠,當街刺殺李鴻章,最后李鴻章雖然沒死,但中槍受傷,把談判耽誤了半天。等到李鴻章恢復過來的時候,他說:“再怎么說,我半條命丟掉了,你總得讓點步”最后才又砍到了2億兩白銀的賠款。談判結束兩個月后,李鴻章病亡。在他閉眼的前一天,俄國代表還在逼著他在條約上簽字,
臨死前,李鴻章留下一首絕命詩:“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三百年來傷國步,八千里外吊民殘。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李鴻章的死,標志著清政府失去了改革的最后機會。而這筆巨額的資金成了日本現代化的原始積累。兩國命運相差,相去何止以里計。
正是甲午戰爭,標志著日本從被殖民的對象變成了殖民別人的對象,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的日本,終于搭上了帝國主義分割世界的末班車。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二十世紀初,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據傳曾向天皇密奏,奏章內容就是日本稱霸東亞的具體方略,史稱《田中奏折》,奏折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日本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如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田中義一的基本邏輯。就是說,日本要想成為強國,在叢林里邊不被吃,要吃別人,那就必須把中國拿下來,吃掉。這個符合他那個時候的邏輯,就是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要先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滿就是東北,蒙就是蒙古。他一直按照這個邏輯,用了將近50年來干這個事情,所以才出現了日本這個小國為什么要吃中國,為什么這么殘暴,首先就是他的帝國主義邏輯。
抗日戰爭的時候,小日本又把中國打得體無完膚,為什么會這樣?兩條:我們暫且不講政治體制的問題,第一是因為當時中國是一盤散沙,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
表面上蔣委員長統一中國,本質上還是軍閥割據。中華民族一旦一盤散沙,肯定被別人宰殺或者內亂。要想強大,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幾千年歷史無一不是這樣的。所以一個是全民皆兵、新崛起的帝國主義列強,另一個是一盤散沙的混亂狀況,就像狼到羊群里面一樣,各個擊破十分容易。
還有第二個問題,很多人都忽略了,這個時候的日本已經是新興的工業國家,中國還是一盤散沙的農業社會,也就是熱兵器打冷兵器。
我這些年在全中國、全世界走,這次我在太行山跟當地人聊的時候,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他們給我看了一些日本戰后的遺物,今天看都很震撼。刀等武器不用說了,連每個日本人背著的飯盒、水壺,做工都非常講究。這就是工業社會來打一個農業手工業社會,當然我們不堪一擊,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經濟業態的碰撞。
現在回過頭來看,今天中國的工業化、制造業已經補上這一課了。中國有一個強大的中央、強大的社會,這一點上美國都是很害怕的。所以中國只要不犯顛覆性的錯誤,不走回頭路,未來真的是不得了的。
第二個邏輯,后來日本戰敗以后,美國有一位女社會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她代表美國軍部分析日本的國民性,探討日本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嚴重的人格分裂,看起來文文雅雅、彬彬有禮的日本人,為什么在戰場上這么野蠻,這么殘忍,這么沒有人性?
后來她寫了一本書《菊與刀》,成了一篇經典的報告文學!揭示日本的國民性。一邊是菊花,很和藹很文明,一邊是武士刀,這就是雙重性格。而這種國民性,我認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地理環境。
日本作為一個島國,資源短缺,土地面積狹小,而且災難多發,火山、地震、海嘯、臺風都是日本的常客,所以導致日本人有著與生俱來的緊迫感和危機感。日本之所以會世界帶來災難,并不是單純的軍國化、右傾化問題,而是日本文化中本身就隱含著對逝去美的追求。這種追求一旦對外,就可能演化成為重大的災難。
“二戰”結束以后,重建世界秩序,聯合國成立,美軍進入日本,改造日本。日本國民性的另一面表現出來了,非常有意思。它全盤接受了美國大兵的統治,而且接受了全盤西化的國體和憲制改革。
這個時候世界的邏輯又走向另外一個端,新的政治經濟格局開始建立,帝國主義殖民化的時代邏輯已經過去了,日本按照這個邏輯去走另外一條路,一不小心30年以后,居然實現了一個它在戰爭里面都沒有獲得的巨大利益,成了世界第二大強國,成了亞洲第一。
甚至我記得90年代初的時候,讀過一本著名美國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寫的《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認為日本馬上要超過美國。日本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功,其實也與日本的民族精神有關。
首先第一點就是有恒產者有恒心,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日本的京都有很多千年老店,十幾代人代代傳承,如果不是建立在個人財產的保護之上,簡直是不可想象的。日本的這種穩定感和政體有關,天皇萬世不易,如果像中國這樣城頭變幻大王旗,皇帝輪流做,每一次王朝更迭就是一次江山傾覆,不可能有這樣的企業存活。
第二點就是匠人精神,關于匠人精神大家說的已經太多,我不多贅言,只講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我此次去日本,到一家街邊小面店去吃飯,店里面的阿崎婆九十出頭,老得背都駝成一座富士山。但一見我們這群專奔她而來的客人,頓時精神抖擻,毫無老態。親自為我們炒飯,炒了二十多分鐘。老阿婆五十來歲的兒子告訴我們,為彰顯這家五十年老店的私廚水平,老太太一早就去牧場選購了最好的但馬牛肉。這就是日本人“一生懸命”的工匠精神。這樣代代傳承的店在日本何其之多,這樣的“工匠”在日本又何其之多。
第三點,就是精細化、精密化的精神,以醫療行業為例,日本利用自己精益管理和精細服務,往往能制造出在國際上有競爭力的產品或服務,并可以參與全球市場博弈。我們發現大部分原始創新是歐美人發明的,但在持續運用與商業運作上,日本卻總能轉化成最好的且最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這是日本“技術立國”的真諦。
在大健康領域,專業與精細不僅帶來的是服務品質的提升,更關乎到生死攸關的問題。我的一位企業家朋友曾經罹患癌癥,在中國幾乎已經宣告救治無效,該富豪赴日本治療后,痊愈而返。事后他感慨萬千地和我說,中國和日本在癌癥治療方面,器械和醫療手段都相差無幾,唯獨精細化、專業化的程度相差甚遠,例如化療,國內可能有癌變細胞的區域一整塊全部化療,日本卻像導彈精確制導一樣,極其精準地進行治療,這是醫學水平的差距嗎?并不是,這就是職業精神的差距。
第二,管理的精益求精。細節決定成敗。日本的細致與認真在全球都是出了名的,日本在硬件配套上、人才服務培養方面都做到了精益求精的管理,使人們不自主的產生“品質、安全、信任”的印象。醫療健康行業的服務人才最需要的就是認真,這是一個醫療健康類企業成功的法寶,推而廣之,也是日本企業的立足之本。
3、中日將進入深度合作期
80年代初期,我正在讀大學,當時的日本如日中天,“以日為師”的口號火遍全國。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只出訪過三個國家,美國、日本和新加坡,布局好宏偉藍圖后,就再不出訪。如今回過頭來看,鄧公的謀篇布局確實堪稱了不起:訪問美國促成中美建交,為中國的長治久安打下了基礎;訪問新加坡表明了以鄰為友,而不是以鄰為壑的態度,不再輸出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以將近75歲高齡出訪日本,接替周恩來與日方會談,推動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小平的日本之行是非常震撼的。他在日本看了鋼鐵廠,坐了高鐵,還將松下等企業都看了一遍。在同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交流會見時,鄧小平第一句話就開門見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我這次是來向你們請教的。”他說,“日本值得中國學習的東西很多。松下老先生,你能否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幫點忙?”非常謙虛與誠懇。在日本掀起一陣“鄧旋風”后,小平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一定要跟日本交好,捐棄前嫌,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日本。
后來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也去了日本,把中日友好的氛圍燃燒到了一百度。當時我這樣的大學生也在拼命學日本,學日本的歷史、學日語、還有學豐田管理方式等等。
那個時候日本有一批老人、老企業家覺得有愧于中國。當時小平表現出來的誠意也讓他們捐棄前嫌,他們在幫助中國上真的是不遺余力,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現在特朗普吐酸水,說是他們幫助了中國,中國虧待了他,這個純粹扯淡,真正幫助中國的是日本。包括在貸款上,在援助上,包括中國的工業化前期,他們都提供了很多幫助。民間更不用說了,我見了很多日本人對中國都非常友好。
但后來中日鬧崩,除了領土之爭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萬萬沒想到,中國在短短的一代人時間里,就從一個受援國,一個弱不禁風、被憐憫的民族,一個他們有愧,想施舍的民族變成了一個超過它甚至是取代它的國家。這點日本人很難接受,思想上轉不過這個彎。
日本的政治和經濟學家曾經提出過一個理論,叫作“雁陣理論”。甚至是從甲午戰爭開始,日本開始以東亞的龍頭自居,按照吉田茂的《激蕩的百年史》所言,日本一直承擔著拯救亞洲于水火之中,使亞洲擺脫白種人奴役的重任。從“大東亞共榮圈”到雁陣理論,無不體現了這一點,日本是頭雁,中國是尾巴和身子,中國龐大的資源和龐大的市場支撐起日本的制造業與服務業。在這種模式里,日本人吃肉,我們喝湯。但日本經濟學家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中國又要吃肉,還喝湯,而且還在短短的四十年中,完成了從“湯”到“肉”的轉變, 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日本夾在中美之間,而且自戰后到現在,日本一直處于美國的附庸地位,當美國帶頭要遏制中國,打壓中國的時候,所以作為一種本能的取向,日本也會隨之圍堵中國。但打了十年八年,中國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反而一路高歌。日本人是一個很實際的民族。特別是政治家們,譬如我們一向比較反感的安倍晉三,他也是日本戰后在位最長的首相。安倍之前,日本七年換七相,他成功地走出了這個陰影,創造了日本政壇戰后最大的奇跡。
就是這樣一個政治人物,搞不好可能會成為中日之間的橋梁,雙方真正的捐棄前嫌,共同攜手合作,成為在東亞經濟圈破冰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在這個背景下面,建立中日韓東亞經濟圈,如果沒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反而比歷史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變成現實。
當年我們認為尼克松是美國資產階級最大的反動派,最極右的人士,但最后是他來訪中國,開啟了一趟破冰之旅。1972年的春天,毛澤東和尼克松會面的時候,意味深長地說道:“我喜歡右派”。因為右派是最務實的,講求實用主義,能夠拋開意識形態之爭,也正因為尼克松是最大的右派,中美兩個死冤家才能走到一起。
和尼克松一樣,安倍也是一個超級右派,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他可以對特朗普卑躬屈膝,也可以和中國捐棄前嫌,精誠合作,不管你喜不喜歡他,恨不恨他,都無所謂。為了民族利益、國家利益,而且他本身有穩定的政治地位和話語權,他反而有能力促成或者做成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
他已經深刻地認識到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他還深刻地認識到,面對美國的持續走衰,特朗普的胡作非為,日本要自保,要繼續發展,必須跟中國捆綁。
今天的社會已經表現得很典型了。中國巨大的購買力和消費力是整個日本經濟強勁發展的很重要的支撐。前些日子,日本政府公布了2017年接待外國旅游人數。在過去的一年里,共接待外國游客2900萬人次,其中前11個月,中國大陸就有679.15萬人次,名列日本國外旅游人數首位,而臺灣也有424.46萬人次,加上香港的200多萬,其中近一半是中國人。據統計,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赴日游客突破400萬人次,有數據預測,全年有望超過800萬人次。潮水般的中國游客去消費日本的服務,消費日本的盛唐盛世,洋風和魂,消費日本的產品、醫藥、食品,這些都是日本經濟的重要支撐。
800萬人赴日本,對中國而言也是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現在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這種向往,在日本一一得以實現,這座萬億級的金礦有待更深入的挖掘。
4、從熱戀到婚姻:利益永恒
當今國內,尤其在互聯網上,反日仇日的言論相當激烈,這和歷史遺留的問題有關,也和近年來主流的輿論導向有關。我在8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日本電影在全國風行,《追捕》《血疑》等片家喻戶曉,銀幕上杜丘跟真由美騎著馬在日本的東京街頭逃竄,銀座、新宿、澀谷的車水馬龍,霓虹燈閃耀。日本的現代繁華,跟我們中國灰頭土臉的城市景觀簡直是天壤之別。
那時的中日關系迅速升溫,胡耀邦邀請3000名日本青年訪華,在招待方面,親自叮囑:友好是最大的政治。
而近十幾年來,“抗日神劇”大行其道,電視電影里幾乎找不到日本人的正面形象,一提起日本,就馬上聯想到鬼子。民間尤其是互聯網上,對于日本的看法也偏向于妖魔化、極端化。愛國激情固然可嘉,但愛國也要建立在冷靜的分析和思考之上,正如周恩來總理所言:對日本既要正視60年,但也要考慮兩千年。從甲午戰爭算起,日本侵略我們長達60年,中國受到了無可估計的損害;另一方面,日本和我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從漢唐以來就有悠久的友好交往,日本從人生哲學、經濟文化、到生活習慣,和中國都有切割不斷的聯系。這樣的態度,才是客觀的。
回顧過往40年,中日之間的政治和外交關系時有陰晴冷暖之變,兩國間的經貿關系卻始終以相對平穩的態勢朝積極方向發展。這正是一種沉默的智慧:兩個東亞大國間的依存關系,首先是切身利益所需,既不必期待過高,也無需矯枉過正。安倍返回到“羽田的青空”之后,中國需要面對的依然是一個既有回暖雙邊關系的意愿、同時仍對中國安懷戒心的日本。
打一個很通俗的比方,80年代的中日友好就像青年男女熱戀,感情迅速升溫,滿嘴山盟海誓、甜言蜜語,“3000日本青年”訪華就是典型的戀愛心理,但浪漫終究不能當飯吃。歷史的進程也果然體現了這一點,陰晴冷暖、幾度變化,中日關系跌宕近四十年。
和戀愛不同的是,很多半路夫妻反而能一路走下來,相互扶持,其原因在于雙方都成熟了,能夠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討論問題,是和是離,歸根結底,逃不開“利益”二字。從戀愛到婚姻,中日關系也是如此。
時代的發展,從不以個人好惡為掛礙,下一步中日之間,如果沒有突發的、重大的危機,從趨勢上來講,將會走向更深一步的經濟合作,這種合作,可能就在不遠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