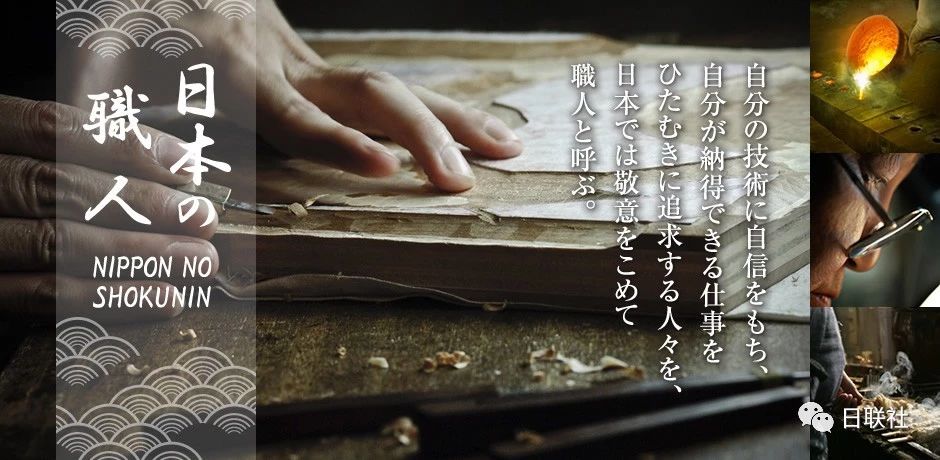“日本沒有那么美好,也沒有那么恐怖”
作者/圖片:李忠謙 來源:風傳媒
龍應臺基金會11月3日舉行思沙龍活動,由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以“歷史的記憶、歷史的忘卻—日本,這個不成熟的民主國家”為題,輕巧而溫柔地帶著聽眾一起檢視了她對于戰爭記憶、歷史記憶的觀察。
阿古教授非常重視教育與批判思考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過她也對臺下的聽眾畏懼“強大的日本可能發動戰爭”感到驚訝。
阿古說,日本人并不像臺灣人想到那樣團結、那樣美好,內部也有很多矛盾與缺點,但她也同樣不希望再看到日本發動戰爭,會以學者的身份繼續努力。
戰爭與歷史的記憶,每個人都不一樣
阿古教授說,戰爭與歷史的記憶,與每個人的背景密切相關,所以她也介紹了自己的成長背景與經歷。
阿古智子其實并非歷史或戰爭的專家,她1971年在大阪八尾市出生,在大阪外國語大學主修中文。后來在香港大學拿到教育學博士后,以一名社會學者的身份在中國研究現代社會的變遷,關注留守兒童、維權律師、公民社會等議題。
阿古教授說,她從小在大阪郊區的八尾市長大,那個地方有許多“部落人”(江戶時代社會地位最底層的人)、被強迫來日工作的朝鮮人、來自中國貧困地區的留學生、政治犯的孩子。
這樣有趣而多樣的社會組成,讓當地的老師非常重視“反歧視教育”,當時老師編纂使用教材的自由度也比現在高。
可能也是這樣的生活經歷,阿古說,她在北京的家空間雖然不大,但總會保留一兩個空房間,給來自中國貧困地區的學生住。但她也說,可惜大阪的左派傳統沒有保留下來,如今大阪的政治氣氛已經變得非常保守。
阿古教授說,自己原本沒有想當老師,而是想到國際的NGO從事一些扶貧的計劃。不過到香港大學念書之后,才以一邊做計劃、一邊讀書的方式來對中國進行理解。
阿古后來到中國做田野調查,也同樣喜歡深入社會底層,所以她不喜歡跟她的老師輩出訪,因為這些學者多半是跟當地官員喝酒,然后取得研究所需的資料,“這樣就看不到當地人民比較草根的生活了”。
我的戰爭記憶
阿古智子教授說,二戰的時候她的父母還小,自然不可能上戰場,包括她的祖父母同樣沒有上過戰場,她笑著說:“所以我對靖國神社沒有什么感情,因為我的家庭沒有這種背景。”
但阿古先生的爺爺確實到南京附近打仗。阿古說,她的公公是一位三重縣的農民,在中國作戰時受傷,中國人救了他之后就被送回日本,“但他從來不告訴我們發生過什么事情”。
阿古的公公自己有兩座山,從林業方面的工作。他住的村子非常寧靜而樸素,村民都是從事放牧或耕種的工作,不過當戰爭爆發,村子里三分之二的百姓都上了戰場,大家都要為天皇與國家效力。
他們根本不理解紀錄片所說的事實:日本在根本不可能打贏的情況下作戰。不過阿古的公公是一位自民黨的黨員,雖然參與并不積極,但為了領取退休金,所以還是選擇支持自民黨。
“我青春期的很多煩惱,都是這些老太太替我媽媽聽的”
阿古也談到,她在撰寫博士論文時,曾在上海一個老媽媽家借住了一年。由于阿古自己的媽媽在阿古初中時因為癌癥去世,所以在她成長的過程中,有機緣認識了幾位中國的老太太,“所以我青春期的許多煩惱事,都是這些老太太替我媽媽聽的”。
阿古教授特別提到上海的老媽媽,因為她在二戰時吃過日軍的苦,文革后又被斗爭的很慘。不過這位老媽媽也是個很忠貞的共產黨員,總是為了黨、為了國家貢獻,像阿古老師這樣日本學生到中國留學,她就會負責接待照顧,不過這位老媽媽前兩年已經去世了。
周遭人的戰爭記憶
阿古智子教授說,她因為家人都沒有參與戰爭,所以她的戰爭記憶都是透過學校的教育(大阪的公立小學、公立初中)而來,還有像是上海老媽媽,甚至從不愿透露他的參戰經驗的公公。
阿古表示,就算公公什么也不告訴他們,他們還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事情。有趣的是,阿古教授也介紹了她的8歲兒子的“戰爭記憶”。
阿古說,他的小孩是東京都中野區的“平和之森小學”的二年級學生。
“平和之森小學”的校地過去是專門關押政治犯、思想犯、無政府主義者、參與工運的老百姓的中野監獄,但如今只剩下美麗的紅磚校門還是監獄遺跡。由于日本小學現在都會教授孩子們當地的歷史,阿古就問孩子的老師,是不是會教導孩子相關的歷史?沒想到老師說,這不在國小的教育范圍里。
平和之森小學的鳥瞰圖。
阿古智子說,如果要知道日本走向戰爭的道理,包括思想控制的那些黑歷史,都應該要去學習跟了解才對。
后來阿古提議在學校辦一個工作坊,也畫了海報,結果老師還是說“不可以”。阿古問為什么,老師說,這張海報上有納粹、政治犯等詞匯,超出孩子的學習范圍了。
阿古批評,為什么日本學校的教育體制會這么樣的僵化。
平和之森小學新址內的中野監獄大門。
此外,平和之森小學因為準備遷校,新址上留有的中野監獄該不該拆除,也成為學校與老師、家長爭論的話題。
不過許多日本人都抱持著不想“惹爭議”的心態,不想跟政治話題沾染上關系。這個案子目前還在中野區討論,已經開了兩次公聽會與討論會,預計11月底才會有結論。
阿古說,日本的教育非常欠缺批判思考,透過對這些遺址的保留與保存,除了可以認識過去,也可以作為舉辦沙龍之用。
“我覺得日本其實很可怕”,一位現場聽眾提到,她曾經參加各國軍艦在雪梨的活動,在看了不同國家的軍艦之后,讓人印象最深刻的還是日本軍艦,最干凈、最有禮貌,就算是其他很強的國家,也沒有辦法達到日本人的有紀律、有禮節的程度——這才是大家最怕日本的地方。如果未來中日還有一戰,中國真的打得過嗎?
阿古教授在回答時苦笑著說:“你們那么害怕日本人,該怎么辦?”
她認為這些對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你們的幻想”。她自己看日本人的小孩子根本不守規定,但有一點讓她擔心的是,日本有許多不合時宜、甚至不合理的規定,但社會都不愿意去改變。
像是公立學校的家長會都在白天舉行,這讓上班的男性與有工作的婦女都沒有辦法參加,她曾建議校方改到晚上舉行,但校方不愿意改。這到底有什么道理呢?學校也說不出來,只知道一定要遵守,整個日本社會這樣的情況非常常見。
從這個角度出發,阿古說“我能理解你們為什么害怕日本人,因為有時候我也害怕。” 因為日本這種集體的慣性讓她很不舒服,她認為日本社會應該跟臺灣學習比較靈活的態度。
還有聽眾問到,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又不愿意道歉,跟日本的民族性是不是有關?
阿古老師認為這個問題他很難回答,因為日本也有各式各樣的人,在政治問題上也有左派右派的多樣觀點。日本在國際化之后,像她這樣在各國之間跑來跑去的人也很多,也會不習慣日本的傳統文化,你們認為日本人很團結,但日本人并不是你們想像的那樣團結。
日本的左與右
阿古說,她這幾年開始往臺灣跑,對臺灣的理解還非常不夠。她發現臺灣的老百姓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立場,所以要跟臺灣人交朋友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不要說錯話。
而日本左派與右派的立場與爭議也是一樣,也影響到日本人對戰爭與相關問題的態度。
自民黨一般來說被視為右翼(保守派),重視穩定與現實、傳統與秩序,因此同意保留天皇系統、支持國旗國歌、夫妻同姓(太太婚后改為夫姓)、反對外國人的參政權與投票權;立憲民主黨與共產黨一般被視為左翼(革新派),更重視人權與自由平等,夫妻可各自保有本性,支持外國人的投票權與參政權。
阿古智子教授指出,其實不同年齡層對同一個政黨的左右傾向往往會有截然不同的判斷,甚至可能橫跨左與右,像是圖中的日本維新會(黃色)在年輕人看來竟然是一個左派政黨。(李忠謙攝)
不過阿古教授也提醒現場聽眾,事實上左與右存在非常多細膩的分別,以上的分類并非絕對,所以對于道德觀的沖突應該盡量去了解才對,而不是簡單的貼上誰好誰壞的標簽。
更有意思的是,左翼與右翼的含義在不同時代也不盡相同,甚至同一個時代的不同年齡層也會有不同看法。像是日本維新黨是非常右的,但在二三十歲的民眾眼里,卻是liberal的政黨,自民黨在年輕人眼中卻是一個中間政黨。
不過現在日本的右翼比較容易受到支持,左翼比較不受歡迎。可能是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可能鬧的太過分了,引來社會的普遍惡感。
慰安婦與假新聞
阿古智子在座談時聊到臺灣先前的慰安婦雕像被踢爭議,她說這件事讓她感覺非常丟臉,并強調那些都是極右派分子所為,并非一般日本人的態度。
不過她也提到,《朝日新聞》2014年前曾經撤回數十年前的慰安婦報導,因為采訪對象吉田清治說謊。這起事件引來右派政府與《產經新聞》等右派媒體大肆攻擊,連一般民眾都受到影響。
阿古說,她一個朋友的先生是法官,家里因為要幫小朋友訂兒童報,她的朋友就選了《朝日》,結果他朋友的先生非常不高興,說“為什么訂這樣的報紙”,可見《朝日》的慰安婦報導爭議在社會上的影響。
不過阿古也強調,《朝日新聞》的幾則報導確實有問題,但這并不代表所有慰安婦的相關資訊都是錯的。
若把左右之爭帶入日本憲法的修正爭議,這時右翼反倒是“革新”的一派,左翼則是希望保留現有的憲法內容。因為右翼認為現行憲法是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所制定,日本應該根據固有傳統制定(修改)憲法,第9條當然可以修改,更右的意見甚至希望回復舊有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主權不在民而在天皇;左翼則認為日本現行憲法保有外國的革新思想,與大日本帝國憲法相比,沒有必要修改。
日本左派與右派的問題
自認并沒有特定政黨偏好的阿古,也指出日本左派的問題:他們常常過度重視中日友好。
像是她很多做中國研究的老師都是偏左,他們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時常常只跟官方打交道,承接一些中日友好的項目。但阿古教授批評,她的這些老師輩并沒有跟民間人士打交道,以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中日友好是假的,不是真的。
阿古說,像她一樣關切中國人權問題的日本研究者,往往都是右派,但這些人的問題是,常常利用研究成果煽動對中國、朝鮮的仇恨,進而歧視這些國家,這也是她無法贊成的。
還有一些日本右翼常跟臺灣獨立派合作,過度美化日本。阿古教授笑著說:“日本不是那么美好的國家,有很多問題的!”
阿古教授認為,日本的民主主義之所以不成熟,是因為缺少能夠獨立思考的年輕人,這一點要仰賴教育的變革才能逐漸改善。至于左右之間、或者不同立場的碰撞,則牽涉到彼此是不是能夠理性溝通、超越自己的局限。
她在演講中也提出四個建議:盡量客觀了解道德觀的沖突、面對事實、尊重專業主義、維持耐性。
她最后呼吁,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主體性,要小心可能會利用你的勢力,每個人也要堅持誠實的態度,不要只是考慮自己利益為主的那種立場。
阿古智子。(李忠謙攝)
阿古教授表示,戰爭是人類的災難,我們一定要弄清楚這種災難是怎么發生的,否則戰爭還會再發生。現在日本的媒體時常強調中國與韓國的缺點與反日情緒,這難免讓日本的年輕人不高興,覺得中國與韓國為什么這么仇日。
與此相對,阿古說,東京大學跟北京大學不久前辦了一場研討會,討論社會弱勢的問題。北大學生的程度非常好、討論能力非常強,但他們說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非常好,反倒是沖繩人沒有少數民族地位,總是遭到歧視。阿古也批評,北大學生的觀點太過簡化,這一定程度都是受到媒體與宣傳的影響。
對待戰爭責任,德日為何不同?
對于日本人不愿意承認戰爭責任的問題,阿古說也有很多日本人承認戰爭的責任,日本政府(尤其是社會黨執政的年代)過去也曾經道過歉。
至于為什么日本與德國對待戰爭責任的態度有所不同,阿古認為跟冷戰時期的局勢有關。
日本選擇跟美國合作,站在資本主義陣營反對共產主義,這一點跟臺灣很像。阿古說,臺灣人會那么喜歡日本,其中也有冷戰的因素。德國在戰后隨即開始賠償、教育的工作,但是日本戰后跟中國分屬兩個陣營,就沒有很好的處理這一件事。1970年代的中日交流與友好并不是民間自發,而是雙方政府基于外交需要所營造出來的,戰爭的相關問題還需要民間與政府一起努力,民主國家也應該一起合作對抗反民主的因素。
采訪側記:日本人(該)是什么樣子?
在阿古教授的演講之前,現場先播放了一支紀錄片—《石原莞爾將軍:發動戰爭的男人》,講述“大東亞戰爭”的理論指導者石原莞爾中將的故事。
正當觀眾沉溺于一位日本將軍發動侵略的理論與現實之中,一位個子嬌小的東大教授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剛才看了這個紀錄片以后,我自己作為日本人,覺得有一點害怕、有一點恐怖。”
這位教授正是當天活動的主角人阿古智子,她說,日本人并不常看這樣的戰爭紀錄片,日本的小孩子也不怎么有機會看,所以覺得比較恐怖。
從這個看似閑聊的開場,卻點出了一項事實。距離今日已超過70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已經沒有多少人真的親身經歷。
而日本人與臺灣人對于中日戰爭的面貌與記憶,在不同的歷史教育與政治宣傳之下,真的會指向同樣一組歷史事件嗎?
年齡在73歲以下的中日民眾,其實就根本沒有機會親自見證二戰,大家都免不了是透過教科書、各種媒體與口耳相傳,來理解中日戰爭。
作為日本的鄰國、以及曾被日本侵略與殖民的國民,看了講述日軍參謀如何謀劃發動侵略戰爭的紀錄片,感覺當然不怎么好受,現場也有好幾位聽眾表達了對強大日本的恐懼、以及對日本可能再次侵略鄰國的擔憂。
經常造訪中國、先生也在北京擔任駐外記者的阿古教授說,臺灣人對日本的印象讓她很意外,日本人沒有那么厲害、那么團結,但她也希望日本更多些靈活性,不要只知道服從與守舊。
透過紀錄片所展現的日本將軍形象,跟眼前這位實際站在眼前的日本學者,那個才是我們印象里的日本人?那個才是日本人的真面貌?
除了阿古所說的“日本也有各式各樣的人”,也如同現場一位聽眾所說的,阿古教授給人的感覺“是個不太像日本人的日本人”。
如果有更多像阿古教授這樣理性的聲音能夠發揮力量,也許日本的鄰國也不用在二戰已經結束的七十多年后,還要繼續“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