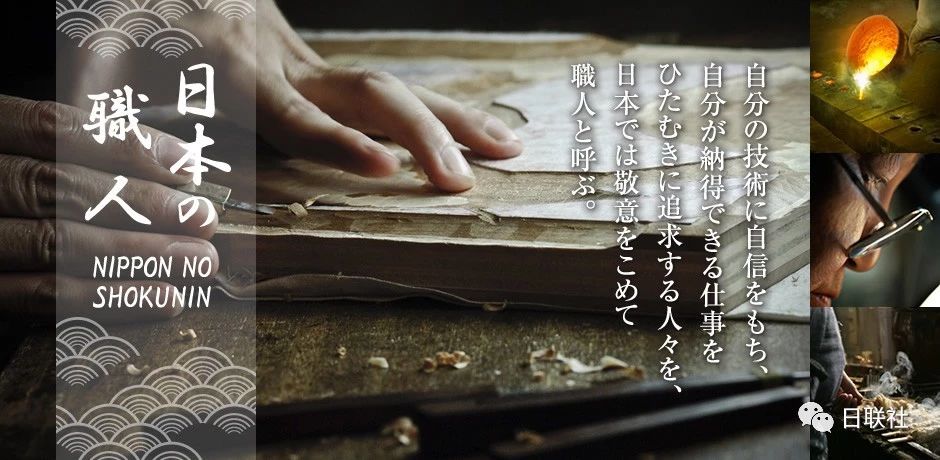日本最大的醫療集團是如何煉成的
文/新浪財經日本站站長 蔡成平 特約記者 何婕
創業僅短短40年的的德洲會,如今已成長為日本第一大、全球第三大醫療集團,在日本擁有385家醫療設施及養老、看護機構,已在全球28個國家和地區展開國際醫療合作。德州會是如何短期內迅速崛起的?其成長之路,又能給中國的醫療帶來怎樣的啟迪?
 日本最大醫療集團是如何煉成的
日本最大醫療集團是如何煉成的
提到德州會,中國人恐怕大多聞所未聞,甚至當筆者問國內的(醫療)業內人士時,他們甚至也大多知之不詳,更有甚者還反問道“德州?哪個德州?是山東的那個德州嗎?”……
但在日本,談到德州會,幾乎盡人皆知。創業僅短短40年的的德洲會,如今已成長為日本第一大、全球第三大醫療集團,在日本全國擁有385家醫療設施及養老、看護機構,且目前已經在全球28個國家和地區展開國際醫療合作,未來的目標則是要進入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
德州會,是如何短期內迅速崛起的?其成長之路,又能給中國的醫療帶來怎樣的啟迪?帶著這些問題,筆者再次走訪德州會總部,并如約見到了鈴木隆夫理事長。
原點:唯有生命是平等的
“德州會”這個名字,與集團創始人、前理事長德田虎雄有密切關系。德田虎雄被譽為是日本的“醫院王”,德州則是德田虎雄的故鄉——鹿兒島縣“德之島”的別稱,是日本的一個偏僻的離島。如今的德之島,擁有日本極高的出生率,約247平米公里的海島上生活著約27000人。
但是,故鄉帶給德田虎雄的不全是美好的記憶。在他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年僅3歲的弟弟突然病逝,當時為了給弟弟治病,德田虎雄晚上行夜道徒步去求村里的赤腳醫生,但醫生并不能及時應對。當時的德之島,因地處偏僻,沒有像樣的醫療設施,島民一旦得病,即使本非致命的大病,也往往因為沒有錢或來不及去本洲治療而喪命,德田虎雄的弟弟便是其中的一例。
這件事對德田虎雄的影響極大,影響了他一生的事業選擇。幼年的他立誓寫道:“為醫者,在急病患者面前,不管患者是誰、無論有什么理由,都應予以治療。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但現狀卻讓人遺憾,既然如此,那么我要成為醫生,去救助患者及困窘之人。”
此后的德田虎雄全力為實現這一夢想而努力,歷經兩次高考落榜,最終考入大阪大學醫學院。為了支付高昂的醫學院學費,他大學時代的打工干過家教,也干過苦累體力活。醫學院的實習,讓他更深入目睹了赤裸裸的醫療現實:農村及偏僻離島的醫生嚴重不足、公立醫院面對急病患者推諉敷衍、因為沒錢等原因而得不到及時救治的患者……
德田虎雄曾回憶道,“我大學畢業的1965年,當時的日本救急醫療體制非常粗糙,這一實態讓我感到愕然。比如,國立或公立醫院在營業時間外、周末、假日等不接診,患者像被踢皮球一樣的踢來踢去。私立醫院在營業時間外,則只接確保能賺到錢的患者,那些看上去不太能賺到錢的患者也是被拒診的。
 新浪財經專訪德洲會理事長鈴木隆夫
新浪財經專訪德洲會理事長鈴木隆夫
我原本以為只有德之島那樣的偏僻地方才會出現我弟弟那種眼睜睜看著死去的慘劇,后來卻發現其實大阪這樣的大城市也是如此。當時,我在實習醫院里拼命說服醫生搶救一些患者,確實很累。但疲倦了休息下就可恢復,而患者的生命一旦失去了就再也回不來了。”
為了改變這一被麻木默許的現狀,德田虎雄立志決心打造“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人,都可得到良好治療”的醫院。1973年,35歲的德田虎雄在大阪府松原市成立了“德田醫院”(即目前的松原德州會醫院),并在1975年成立“德州會”,打破公立醫院周末、夜間、假期休息的做法,提出“24小時365天營業”、“不拒絕救急”等方針。
不僅如此,德田虎雄還提出了三個理念原則——“唯有生命是平等的”、“可以安心托付生命的醫院”、“守衛健康與生活的醫院”。基于幼年的痛苦經驗,德田虎雄在發展壯大德州會時堅持走毛澤東式的“農村包圍城市”路線,雖然也在大阪等大城市開設醫院,但更多地是扎根日本地域社會,他公開放話稱:“離島及偏僻地區的醫療,即使赤字也要做!做不到這一點,德州會便沒有存在的價值!”
他在集團主頁上也公開闡述道:“不斷新設醫院,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深感需要向那些因醫生不足而受苦的離島、偏僻地區派遣醫生。德州會的原點是維持并發展離島、偏僻地區的醫療,就算排除萬難也要推進,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在大城市地區經營醫院來協助。”
“政治的原點在福祉,福祉的原點在醫療,醫療的原點在救命、救急。……若假我以權力,國立及公立醫院自不必說,所有不能實施救急醫療的醫院,都應該即刻讓其倒閉。”德田虎雄在一次媒體采訪中如是說道。
所謂“有言實行”,德田虎雄并不止于言,而是伴之以大膽的行動。這讓德州會的觸角迅速延伸到了日本各個地方,從最南端的沖繩一路開花到最北端的北海道。以德洲會的旗艦醫院——湘南鐮倉綜合醫院為例,目前已連續數年救急、入院患者人數排名日本第一,每年接待急診患者約5萬名,現任理事長鈴木隆夫此前便長期擔任醫院院長,他提出不要滿足于日本第一,要將湘南鐮倉綜合醫院打造成“東洋第一”的醫院。
日本的某位國會議員曾評價道:“像他(德田虎雄)那樣富有天賦和卓越領導力的人,在日本政界都找不出第二人來。如果沒有他,日本的偏僻地及離島的醫療肯定要落后若干年。”
讓醫生不收禮成為常識
 德洲會理事長鈴木隆夫
德洲會理事長鈴木隆夫
除此之外,德田虎雄還徹底解決了日本醫療界曾經的一大弊端——收受紅包。他開班醫院后不久即提出,“嚴禁從患者處收禮,一個橘子都不能收,違者即刻解雇。”他甚至放言,“如果是我太太收了禮,我就立刻和她離婚。”
這遭到了日本醫師會很多醫生的激烈反對,日本醫師會是日本最大的醫生聯合組織,號稱有16萬會員,也是自民黨最大的資金金主之一,很多醫生公開批評德田虎雄“破壞了日本的美德”,醫師會也動用政治資源對德洲會進行絞殺。
德田虎雄在1998年出版的《不收禮的醫生》一書中寫道,“當時日本的一些醫院也打出了堅拒禮物的口號,但私下還是有不少醫生在收禮,在很多醫生的觀念中,甚至將從患者處收取禮物當成了理所當然的常識,這些禮物并不僅僅是禮品,還包括了金錢。”
德田虎雄披露稱,“很多大學附屬醫院的教授,以收禮的名義,每月收取數倍于自己工資的好處。公司的總裁或知名人士,經由熟人介紹到知名的醫生處做個心臟手術,如果操刀的醫生是醫學院教授,則需要送30萬-100萬日元不等的禮,操刀醫生旁邊的三位助手也需要各送20萬日元左右的禮,再加上需要打點麻醉醫生、護士的禮金,總共需要送禮約200萬日元,這幾乎成為了醫生行業的‘常識’。而如果沒有熟人介紹,讓醫學院教授為自己操刀的機會都沒有。”
實際上,德田虎雄作為新人剛成為醫生時也收過禮,“是某家公司總裁的女兒來住院,辦理住院手續時、手術前、以及出院時的禮金各10萬日元。而當時作為新人醫生,一個月的薪水才只有10萬日元左右。我在34歲之前就已經有了7個小孩,而且當時還需要援助在讀醫學院的三個弟弟,所以從患者處收到這樣的‘禮’很感激,但感激的同時則是良心的不安。”
“那些收取患者禮物習以為常的醫生經常說,‘其實不管有沒有禮物,在診療時都不會區別對待’。但那是明顯的撒謊。醫生也是人之子,一旦收取了金錢禮品,就會對患者珍視一些,甚至可能會根據金錢禮品的多寡,來決定治療的順序。……我年幼的弟弟之所以當年眼睜睜地看著死去,就是因為家境貧寒,對他的治療不在優先順序中。”
基于這樣的理念,德田虎雄才提出了“唯有生命是平等的”,德洲會自創辦以來便一直杜絕醫生向患者收禮。“有些醫生已經收禮成癖,但這樣的‘常識’必須扭轉,讓真正的‘常識’得到回歸。”
醫療領域的知名媒體人富家孝就評價道,“有時德田很強勢地推進地區醫院的建設,或許打亂了地區醫療的既有格局。但通過成功地抵抗住了醫師會等既得利益層的阻力,讓日本全國各地的救急醫療得到了大發展,他在醫療界留下了重要的足跡。”
對于自己如何能在既得利益根深蒂固的醫療界殺出一條光明大道來,德田虎雄用一句話總結:“努力、努力、再努力!勉強的努力、白費功夫的努力、不惜一切代價的努力,堅持這樣做,則必定會柳暗花明、金石為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