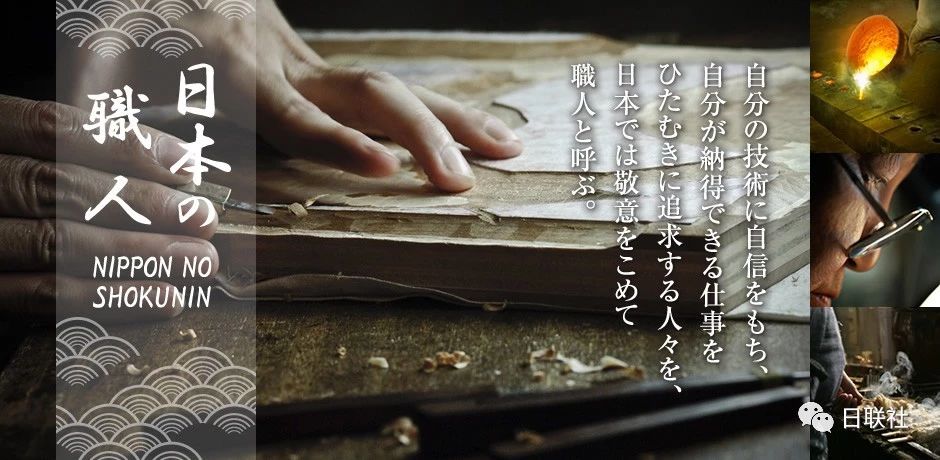最近十余年來,是否采納“夫婦別姓”制度在日本時常成為政治議題,相關爭論也有日漸白熱化的趨勢。依據日本于1947年實施的民法典第750條規定,男女雙方在登記結婚時,必須改稱男方或女方的姓氏,這就是“夫婦同姓”的法律依據。
當然,這種可選擇的同姓制度與此前民法、即1899年實施的明治民法所規定的女方必須改為戶主姓氏(入贅等特例除外)的“夫婦同姓”相比,因其形式上的平等,堪稱法律上的進步。
問題正出在這條看似平等的民法條款上。在婚姻實踐中,這一條款事實上導致了以女方放棄原姓而采取男方姓氏、即“改姓”的結果。19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開始鼓勵女性“社會進出”、即促進女性進入社會生活領域,這種改姓給女性帶來了許多不便。這樣,在前述民法條款中加入“男女雙方可以使用婚前的原姓”就成為水到渠成的解決方案。
為此,日本法務省在1996年與2010年,先后兩度準備了相關的修正法案。然而,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每每引發各種爭議,并最終因各種反對而未能提交至國會審議和表決。
反對民法修訂的人認為,“夫婦別姓”制度不符合日本社會的傳統,將導致“家族紐帶松散”與“家庭解體”,最終造成社會混亂。
而贊同者則認為,現行法典的夫婦同姓制度,并非日本自古以來的傳統,而是明治時代的新發明;它造成了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損害了婚姻當事者的自主決定權。
雙方各有論據,爭執不下。比如,后者會舉現代中國、韓國的事例,認為夫婦別姓制度不會造成任何問題,而前者則舉出俄國十月革命后婚姻制度的激烈變革所帶來的“惡果”,包括離婚率大幅升高、出生率下降以及子女教育的怠慢等,來證明維護傳統婚姻與家庭價值的重要性。目前看來,這種保守主義的觀念支配了日本立法者的意志。
其實,在明治民法典制定的過程中,就出現了類似的論爭。作為社會革命的一環,明治政府早在1870年(明治3年)即開始翻譯《拿破侖法典》,并以其為藍本編纂自己的民法典。到了1880年,在法國法學家博瓦索納的主持下,日本再次啟動編纂工作,并最終完成。
1890年,民法典經樞密院公布,決定于1893年起實施,史稱“明治舊民法”。該法典的家族法部分因事關日本傳統習俗,由日本學者自己起草。即便如此,法典一經發表,隨即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比如法學家穗積陳重發表了有名的《民法出而忠孝亡》一文,認為該民法的基本原理、即“家庭是男女自由契約(婚姻)而成立”是一種“冷漠的思想”,是一種“極端個人本位的民法”,它破壞了“為了家嗣永續才行婚禮”的傳統信仰,不符合日本固有的“淳風美俗”。
與這種主張延期實施民法的“延期派”相對,“斷行派”(又稱“自然法派”)則強調法律原則的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普世主義一面,要求日本立即施行這部民法,從而藉此進入文明之國的行列。(江新興:《近代日本家族制度研究》)
我們看到,當下關于維護現行民法中“夫婦同姓”條款的主張,其實與一個多世紀前的民法論爭中的保守派具有共同的認知結構——民法尤其是其中的家族法部分的制定與修改,關乎社會的基本組織結構與原理,具有特定的歷史性和民族性,因而要慎之又慎。
由于現代中國采用了夫婦別姓制度,這或許會讓一部分中國讀者傾向于如下看法:日本當下相關的論爭并非是重要的政治議題,不免有小題大做之嫌;人們或許還會感嘆、甚至暗自贊頌日本社會的這種保守氛圍。日本“夫婦別姓”制度難以實行,至此得到了讓人暫時首肯的解釋。
不過,我們在上述可能的成見上要稍作停留,因為上述說法事實上回避了問題自身。
不錯,夫婦姓名制度對許多社會而言并不是重要的政治議題,但這正是問題的所在——除了特定的社會變動時期,為什么事關婚姻與家庭的制度往往無法成為政治議程的焦點?或者說,為什么人們在婚姻與家庭制度上傾向于保守?
二
從結論上說,這是男權社會的必然現象。作為社會的組織原理,曾經在近現代社會發揮了猛烈變革作用的“種族”與“階級”的虛妄如今已經大白于天下。然而,對于作為同樣社會組織與建構原理的“性別”,盡管女性主義者對其所蘊涵的權力意志與暴力已然進行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揭露,但迄今仍未達到“解放”的水準——如同人們不再依賴“種族”、“階級”觀念來建構更好的生活一樣。
原因在于,當下體現在婚姻與家庭中的“性別”秩序正是男權秩序自身的體現,它無法在男權社會主導的政治秩序中找到另外的表達。
讓人興趣盎然的是,在階級革命的敘事中,這個古老的“男權”曾經得到過特別的關注。比如,在恩格斯有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男權,即男子的統治,被認為是經濟關系的一種結果;進一步說,男權是財產私有制的結果。
因此,只有在資本主義消滅以后,“男子一生中將永遠不會用金錢或其他社會權力手段去買婦女的獻身;而這一代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也永遠不會再出于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擔心經濟后果而拒絕委身于她所愛的男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
與這種未來的純愛相反,在近代形成的家庭結構中,丈夫是資產階級,妻子則是無產者,是家庭的女仆。這種鮮明的對照與斬釘截鐵的論斷,無疑激發了一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奮斗熱情。
從這種基于經濟關系的性別秩序解釋出發,恩格斯對近代文明制度之一的“專偶制”、即一夫一妻制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這種婚姻關系是利害權衡的結果,與當事人雙方的愛慕毫無關系。
然而,這種男權制的成立所導致的問題并不僅僅限于“愛情”的不在;因為妻子“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單純的生孩子的工具”,而這意味著“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正是因為如此,對于女性突破這種男權制壓迫而展現自身歷史存在的事實,比如賣淫制,恩格斯給予了意外高的評價。
從反面來說,這種被認為是犯罪并引發法律后果的賣淫,“只是使婦女中間不幸成為受害者的人墮落,而且她們也遠沒有墮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種程度。與此相反,它敗壞著全體男子的品格。”換個角度說,賣淫制事實上是男子為自己對異性的統治所付出的代價,是社會給予男性的復仇。從正面來說,女性在這種與男性關系中獲得的自由,使得她們有可能展現自身的“世界歷史意義”。
正因為如此,恩格斯不吝筆墨地寫道:“希臘婦女那超群出眾的品性,正是在這種賣淫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她們由于才智和藝術上的審美教養而高出古代婦女的一般水平之上……但是,要成為婦人,必須先成為淫游女,這是對雅典家庭的最嚴厲的判決”;“斯巴達的婦女和少數優秀的雅典淫游女,是受古人尊崇并認為她們的言行是值得記載的舉世無雙的希臘婦女”。
我們在這里看到了革命導師不同尋常的眼界與格局。從這個角度來看,在諸民族的文學與歷史敘事中,亦即在這種主要由男性撰寫的記錄當中,女性進入歷史的方式就容易得到理解。
除了借助男性符號、諸如“從軍”“掛帥”進入歷史外,更多的女性則是因其作為藝妓、作為姬妾的才華、因其對傳統婚姻制度的顛覆而贏得了當時人們的追捧與身后之名。事實上,男子只有在面對這樣的女性敘事與存在時,他才能恰切地理解自身的存在;或者說,這種女性的存在,是男性理解自身時不可或缺的途徑。
三
關于我們習以為常的性別秩序,還有一種與經濟關系截然無關的解釋,即禁忌與欲望;它們因其程度極低的歷史性,將男權制深層的心理與精神結構揭示了出來。這正是我們從法國哲學家喬治·巴塔耶在其《色情史》一書中獲得的啟發。我們將看到,這種看上去繞遠的說明,給人們所見的婚姻與家庭關系背后的性別秩序,提供了更富有洞見與意義的解釋。
在確立“人”自身的概念時,巴塔耶完全借用了黑格爾的概念——否定自然自身以及否定人自身的自然、即欲望,乃是人的本質特征。在否定人自身之自然屬性,即“獸性”時,“禁忌”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比如,有關性方面的禁忌——諸如亂倫禁忌、裸體(尤其是性器官的裸露)禁忌等——就是人得以成立的規則。這意味著,人在性方面的某些行為之所以會被指責為“禽獸不如”,并非是出于道德的憤慨,而是有著字面自身的本來含義——那個被指責的人實實在在地沒有被視為“人”,因為他不如共享了某些人類禁忌的某些“禽獸”。
有了這個鋪墊,讓我們回歸正題。如何理解與當下婚姻及家庭制度并行的各種色情行業、諸如前面提及的“賣淫制”現象的存在?巴塔耶指出,各種“禁忌”之所以呈現出某種恣意性,比如人類對自身排泄物的厭惡,原因僅僅在于它們處于理智世界的外部;或者說,因為這種恣意的規則的存在,理智世界才得以成立,因而“在這個總體性中,色情世界與理智互相補充,地位平等”。這意味著,色情現象的存在構成了人自身以及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然而,在合法的婚姻關系中,男性對女性的占有僅僅屬于理智的世界,因為“妻子沒有變成滿足所有男人欲望的色情對象。一個作為物的妻子……她主要是生育和從事家庭勞動的婦女”;正因如此,對于男子而言,“妓女不亞于結婚婦女,但這個對象是色情的,她從始至終、徹頭徹尾,完完全全是色情的”。這個作為色情的存在,以其對“獸欲”的取代及其固有的美學特征,滿足了居于統治地位的男子的非歷史的心理需求。
問題的復雜之處在于,“引發情欲的美,無論如何,都與勞動對立”,它“具有青春、花朵、春天和新迸發的能量的意義”。從根本上說,“如果妓女生活在閑暇中,她本身就保留了勞動所消減的純粹女性特征,即聲音、笑容和整個身體的溫柔和流暢形式,或對女人的欲望中固有的一種形式要求的稚氣的溫存”。
這意味著僅僅通過“勞動”,僅僅通過對自然的克服,人完全無法成為人自身。人還要在肉欲的誘惑與否定中轉變為“人”。因此,人從未完全克服肉欲,這正是人的自然狀況。
這種狀況與男權制度的結合,就是我們在婚姻史中常見的面相。比如,“三從四德”這個有名的觀念除了維護男權(即“三從”)制度外,還要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亦即除了家庭勞動外,還要求妻子有“婦容”,要有婉娩之柔情。
如此看來,“三從四德”這幾個字事實上完整地涵蓋了婚姻所要承擔、但事實上無法達成的全部社會功能,即男權社會所制定的功能,包括男子不為人知的心理要求。清人陸圻在其所撰的《新婦譜》中勸告妻子,不要對丈夫“游意娼樓,置買婢妾”表示不滿,相反倒應該“能容婢妾,款待青樓”,可謂男權毫不掩飾的自我表達。
四
有必要再次強調的是,這種“男權”并不能簡化為經濟上的支配關系。憑借高度敏銳的社會觀察與解析技法,日本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在《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一書中,從“厭女癥”(misogyny)的角度,將男權在當代日本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表現描繪了出來。
在上野看來,男權首先是一種獲得承認的欲望。美國有名的女性主義學者塞吉維克在《男人之間》一書中提出了“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說法,將“男性是在男性集團中被承認為正式成員后才成為男性”的這種主體化機制揭示了出來。
這種機制同時意味著,同性之間的承認依賴于對異性的排斥。依據這種主體化理論,上野認為,“男人為了成為性的主體而將對女人的蔑視深植于自我確認的核心”的心理機制,正是“厭女癥”的精神基礎。
如果說這樣的“男權”只能存在于同性的男性社會當中,那么女性就是這種男權社會必然犧牲品,而與任何現實的經濟關系無關。這樣說來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當一個男人被嘲笑為“不像個男人”或者“連一個女人也弄不到手”時,這些說法會對他構成致命威脅。
上野對此總結道:“男人集團絕不會承認這樣的男人為一個成年男人,絕不會給予他這個集團的成員資格。這就是雄‘敗犬’比雌‘敗犬’更難承認‘敗’、處男比處女更難啟齒的原因”。
這種意義上“男權”的精神結構,同樣有效解釋了當代日本社會在婚姻與家庭關系上的現狀。如同事關“夫婦別姓”的論爭所表明的一樣,居于統治地位的日本男性在家庭上有著保守的價值取向,而這個保守首先意味著它對婚姻關系中的權力秩序的維護。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社會有著高度發達的色情產業。顯然,男性對這一產業的貢獻,正是源于他們在社會關系中作為“男性”、作為自我認同確認的需要。在男權制的精神結構中,他們這種與色情行業的關系,或者說他們的這種自由與放蕩,完全從他們言之鑿鑿、并信誓旦旦要加以守護的“淳風美俗”中脫落出去。
在男性的視野中,他們通過精細、巧妙地使用“圣女—蕩婦”、“母親—娼妓”、“妻子—情人”、“結婚對象—玩弄對象”等一系列二分法,成功回避了自己的人格分裂。
當然,這種意義上的“男權”可見諸于任何社會,因為它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原理之一。比如,在中國近年開展的偉大的反腐敗運動中,人們看到各種級別的腐敗官員在如下一點上有著驚人的一致:他們都“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關系”,亦即有著數量不一的“情婦”。在迄今為止的解釋中,這種對情婦的占有被認為是與貪污受賄別無二致,是自身道德墮落與不受限制的權力的必然結果。
誠然如此;不過,對情婦的占有欲望以及相關的炫耀更表明的是,它有著比政治權力更廣闊的“男權”基礎。這種對情婦的占有不同于當下相關法紀的嚴厲懲罰(諸如將當事者蔑稱為“通奸”),在社會層面上毋寧說是“花絮”,成為人們的茶余飯后之談資。
進一步說,在人們看來,無論是古老的色情行業的興盛不衰,還是當下占有情婦意義上的“腐敗”,都不過是與現代婚姻、家庭制度并行不悖的各種“越軌”的一種表現而已。對男性這種越軌行為的告發,并不會引發人們特別的憤怒。男性對此的寬容,源于他們的男權精神結構,這可謂自欺欺人;而女性對此的無奈,則源于男權權力的壓迫,以及在壓迫下的某種自我保存之術。這正是前面提及的《新婦譜》中的“箴言”意義所在。
行文至此,我們已然看到,如果認為日本最近十數年間展開的“夫婦同姓”或“夫婦別姓”論爭的根源僅在于民法上的一個條款,或者說只要改動了民法的相關條款問題就可迎刃而解,那么我們就無視了這一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后面的宏大問題。
如本文所述,日本的夫婦別姓問題,有著根深蒂固的男權基礎;而中國社會在婚姻與家庭領域的相關問題,可以說與日本的這一難題共享了完全同樣的精神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