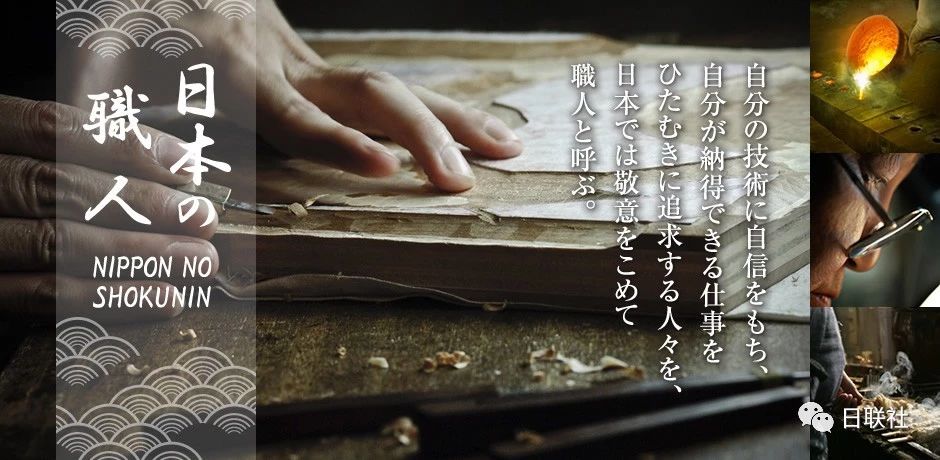在全球化的時(shí)代,任何特定的文化類型常常都意味著一種標(biāo)志差異的風(fēng)格。在這一點(diǎn)上,日本文化無疑有其鮮明的特點(diǎn)——哪怕你沒去過日本,但積年累月在各種圖像、文字中接觸到的那些日本的建筑、器具和藝術(shù)作品,都會(huì)讓你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它們內(nèi)在地具有某種統(tǒng)一的特質(zhì)。

因而,你或許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概括出日本文化的特質(zhì),但當(dāng)你看到時(shí)就能立刻明白,這是日本的風(fēng)格,而不是中國、韓國,更不是英國和美國的。 這種使日本有別于其它文化的特質(zhì)是什么,眾說紛紜,新渡戶稻造認(rèn)為植根于武士道,岡倉天心主張從茶藝去觀察,鈴木大拙推舉禪的精神,而九鬼周造則覺得是在藝伎生活背后的“粹”(灑脫、洗練)。
不過,這些視角往往多是由某一領(lǐng)域的生活實(shí)踐為視角,但“文化特質(zhì)”應(yīng)是某種更根本的存在,即能夠日常性地產(chǎn)生出所有這些生活實(shí)踐的結(jié)構(gòu)本身。岡田武彥認(rèn)為,這種根本性的精神特質(zhì)便是“簡素”。
中國人多多少少也體會(huì)過這種日本式的“簡素”——日本的現(xiàn)代設(shè)計(jì)往往線條簡潔而富于表達(dá),既保守地暗合傳統(tǒng)禪宗精神元素,又往往因其簡潔而顯得相當(dāng)現(xiàn)代。 無論是在裝飾、餐飲還是包裝上,日式風(fēng)格通常不求華麗,而以簡易平淡為基調(diào),追求本色和原味,即便是東京希爾頓這樣的五星級酒店,和式早餐也多可見野菜和蘿卜等尋常蔬菜,而不以花式豐盛、滋味濃郁見長。
甚至在格斗中也是如此,日本的劍道極少華麗繁復(fù)的招式,相反推崇質(zhì)樸有力,如“一刀流”。概言之,日本文化蘊(yùn)含著某種對自然的敬畏(而不像中國人那樣強(qiáng)調(diào)“人定勝天”),更注重本色而拒斥過分人為的修飾添加,強(qiáng)調(diào)對內(nèi)在的靜觀和自我抑制,而非自我彰顯。
岡田武彥在書中說得明白,“所謂簡素,就是表現(xiàn)受到抑制。由于抑制而追求簡素,原有的內(nèi)面精神則變得愈加豐富、充實(shí)以至深化,這就是簡素的精神,這就是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基本世界觀和審美觀。” 他在里面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日本人“立足的根基是未分化的世界”,在文化基因里自認(rèn)相對于“天”和自然是卑微渺小的,采取一種謙抑的姿態(tài),而不像西洋和中國那樣對世界以更為張揚(yáng)、能動(dòng)的積極態(tài)度來面對。 體現(xiàn)在社會(huì)關(guān)系中,便是日語有繁復(fù)到令人頭疼的敬語系統(tǒng),語言表達(dá)曖昧含糊,語句構(gòu)造不以主語為中心,人際交往中不突出自我個(gè)性(張揚(yáng)自我往往倒是令人討厭的)。 他認(rèn)為,這都是因?yàn)槿毡救藢ν獠渴澜绲幕緫B(tài)度是“崇物”的,即自視為龐大自然的一員而非與之對立的存在,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下,人們對物的把握必然是直觀的,而不那么強(qiáng)調(diào)理性認(rèn)識。
如果說這種精神特質(zhì)在日本最為堅(jiān)韌而突出,那或許是因?yàn)槿毡救怂畹淖匀画h(huán)境較為豐足而滋潤——可以想見,對遠(yuǎn)古時(shí)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來說,這個(gè)列島上的森林、水產(chǎn)、植被都是相當(dāng)豐裕的,而與此同時(shí),遠(yuǎn)隔重洋、頻繁地震、海嘯和火山噴發(fā),又使人覺得要掌控自然是極難的。
在這樣條件下發(fā)育出來的人類社會(huì),自然不同于在兩河流域和歐洲文明中那樣強(qiáng)調(diào)對嚴(yán)酷單調(diào)自然的能動(dòng)征服,也不同于中國那樣對人力干預(yù)自然的信念。呈現(xiàn)在思想和生活中,那就是日本人確實(shí)比中國人遠(yuǎn)為拒斥“人工”。
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家)雖然也強(qiáng)調(diào)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但同時(shí)卻歷來強(qiáng)調(diào)“人”的主體性和能動(dòng)性,“人為”在中國思想中也并不含有貶義。
事實(shí)上,中國傳統(tǒng)上很少欣賞純粹的“自然”之美,相反,一個(gè)“人文化了的自然”才是美的,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一座山值得欣賞,不是因其本身的自然景致,而是因?yàn)橛辛恕跋伞边@個(gè)人文性的存在。
在這一點(diǎn)上,日本文化的確比中國文化能更徹底地?fù)P棄外表,靜觀內(nèi)在,它變成了一種對本色的最高贊美,強(qiáng)調(diào)不去觸動(dòng)地欣賞事物本身。
這意味著這種哲學(xué)認(rèn)為平淡簡素是最高的美,它所看到的不是那個(gè)外表,而是外表之下豐實(shí)深厚的內(nèi)在世界——值得補(bǔ)充的是,它之所以格外拒斥外在修飾,恐怕也正是因?yàn)樵谶@樣的觀念之下,任何外在修飾都成了妨礙去體驗(yàn)這種內(nèi)在之美的存在。
這道理也很好理解:如果你喜歡青菜本身的滋味,那么做菜時(shí)放太多醬油調(diào)料,就不再是豐富了菜肴的滋味,而變成了干擾你去品嘗其原味的豐富性了。 不過,盡管岡田武彥一再聲明“簡素”作為日本文化的特殊性,然而不可否認(rèn)的是,他所用以舉證說明簡素精神的原文,一如他自己在書中所承認(rèn)的那樣,“主要還是從中國文獻(xiàn)中引用過來的”。 對這種簡素哲學(xué)的形成尤為巨大的禪宗精神(日語中常有“茶禪一味”、“劍禪一味”的說法,指茶道和劍道在精神本質(zhì)上與禪宗是完全一致的),當(dāng)然也源出中國。
至于主張平淡、樸拙、留白有余味,乃至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大成若缺,在中國文化史上向來史不絕書。如果這樣推想下去,“簡素”二字尚不足以確切地概括這種精神特質(zhì),因?yàn)椤昂喫亍北旧硪彩潜憩F(xiàn)形式,其內(nèi)在精神其實(shí)是“空無”。毫無疑問,最早將這一思想哲學(xué)化的,正是老子在《道德經(jīng)》所說的“無為”、“有生于無”。
當(dāng)然,日本文化很早就表現(xiàn)出其推尚自然的特質(zhì),在其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中,被歌詠?zhàn)疃嗟囊环N花卻是幼小可愛、并不鮮艷的胡枝子,這確實(shí)與中國人在對牡丹、梅花、菊花等的偏好中流露出的審美特性迥然不同。 但恐怕也是中國思想的引入,才極大地推動(dòng)了日本文化的形成。日本人或許遠(yuǎn)在無文字的遠(yuǎn)古就已推崇這種本來之美,但也要到這種新思想的輸入,才能得以形成生活實(shí)踐的結(jié)構(gòu)本身。
就此,內(nèi)藤湖南在《日本文化史》中有個(gè)著名的論斷:“過去日本學(xué)者對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釋成樹木的種子本來就有,后來只是由于中國文化的養(yǎng)分而成長起來的。我卻認(rèn)為比如做豆腐,豆?jié){中確實(shí)具有豆腐的素質(zhì),可是如果不加進(jìn)使它凝聚的外力,就不能成為豆腐。日本文化是豆?jié){,中國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鹽鹵。”兩者的確缺一不可。
雖然書中不止一次舉出托爾斯泰的話說“擁有永久歷史的民族文化,必有其自身的價(jià)值,而不應(yīng)該在與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較中談?wù)撈鋬r(jià)值”,但事實(shí)是,岡田武彥在論證“簡素精神”時(shí),一直是在與西洋、中國的三分體系內(nèi)對照來看的;在這個(gè)參照系內(nèi),他認(rèn)為中國是在西洋和日本之間,但更偏西洋(理性的、人為的、能動(dòng)的、華麗的)。
即便是水墨畫,他也要強(qiáng)調(diào)中日自有不同,而“日本式的繪畫要比中國式的繪畫顯得更為簡素”。他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中國文化理智、理性的一面,但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中以西方為參照系,卻強(qiáng)調(diào)中國文化受感性主導(dǎo)。 這與其說是事實(shí)論述,倒不如說是在什么坐標(biāo)系中進(jìn)行觀察:中國人的比較坐標(biāo)往往是二元的“中西”或“中外”,而日本則自古是三元參照系(天竺、震旦、本朝),現(xiàn)在只是把“天竺”替換為“西洋”,有時(shí)則干脆直接以西方作為參照系,而自視為東洋的代表。
其實(shí)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包含內(nèi)在矛盾的巨系統(tǒng),日本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中也有不同傾向的事物同時(shí)存在(如江戶時(shí)代的浮世繪就極具裝飾性),而“中國”和“西方”這樣巨大的文明,則更為豐富復(fù)雜。 如果說到“日本之美”尚可以用“簡素”二字來概括,那么要以幾個(gè)詞來概括“中國之美”,可就要困難得多了,因?yàn)?/span>中國之美本身就內(nèi)在地多元,恐怕首先得定義“中國”本身。 “簡素”與“空無”本身也是中國文化的源流之一,只是中國文化的復(fù)雜豐富如江河并流,以詩歌而論,所謂“詩分唐宋”(一如歐洲古典傳統(tǒng)中的品達(dá)與賀拉斯),可容納兩種截然不同的風(fēng)格,而唐詩中又可分出許多種風(fēng)格流派,畫也有寫實(shí)、寫意,但日本則善于把一端發(fā)揮到極致。
也正因?yàn)椤爸袊馈碧S富而很難提煉,不幸的結(jié)果之一是:現(xiàn)在的“中國元素”往往變成零碎元素的拼貼點(diǎn)綴而不是內(nèi)在精神的呈現(xiàn),而不像“簡素”的日本風(fēng)格仍以強(qiáng)大的內(nèi)在延續(xù)性提供不斷創(chuàng)新的動(dòng)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簡素”并不僅僅等同于某種現(xiàn)代的“簡潔美學(xué)”。西方文化中也有推崇簡潔的一面,但那種精神導(dǎo)源于古希臘的畢達(dá)哥拉斯學(xué)派,注重的是數(shù)學(xué)、幾何的比例分割(如現(xiàn)代的蒙德里安繪畫)。
即便是“如無必要,勿增實(shí)體”的奧卡姆剃刀原則,強(qiáng)調(diào)的也是去除繁瑣的實(shí)體,其內(nèi)在精神仍是重實(shí)存、理性的特質(zhì),而不是那種強(qiáng)調(diào)事物本來面貌、余味未盡的感受,那種只能感覺而不可分析的感知,所謂“可意會(huì)而不可言傳”,其背后是“空無”。
說起來,這種對直覺、感性的含蓄與余味的推崇,除了對自然界的態(tài)度,恐怕更多地也因?yàn)橹袊⑷毡径际悄撤N“高語境社會(huì)”,在這樣熟人之間互動(dòng)為主的社會(huì)中,人與人之間的很多溝通并不依靠直接說出來的話語,有時(shí)一個(gè)眼神和表情就已會(huì)心。
這與其說是“自我抑制”,不如說是“不需要自我表達(dá)”,因?yàn)檫@種社會(huì)關(guān)系中更強(qiáng)調(diào)“意會(huì)”而非“言傳”,說出來反倒沒意思了。
從這一意義上說,這真的完全是對“本來之美”、“自然之美”的推崇而排斥任何人為痕跡嗎?不,它只是以“不顯示人為痕跡”為宗旨,就像“化妝的最高境界是看不出化妝”一樣,但本質(zhì)上,那仍是一種特殊的人為之美,證據(jù)就是:人們欣賞的仍是這種文化精神,而非事物本身。